我经常听到外婆跟别人讲,小妹啊,已经错过了最好的结婚年龄。后来,我妈跟人煲电话粥的时候,不时也会蹦出几句关于我小姨的话来——别像我老妹那样,错过了生育的好年龄。家庭聚会的时候,但凡说起小姨,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最终都变成了一声声叹息,以及抱怨。我外公固执地认为,小姨念大学,念坏了。据说,小姨上大学前,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优生,大学之后小姨就变了。“抽烟、喝酒、打老K,没有理想,不思上进,整个人颓废掉了!”身为一名中学校长,外公说话总是恨铁不成钢。

关于小姨人生历史上的这次重大转变,家里人至今都不能完全理解。失恋?小姨早就澄清了这个猜测。成绩跟别人比,落差大?小姨撇撇嘴很不屑地说:“弱智,大学生谁还比这个!”那是为什么?小姨发脾气了:“什么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人都一样啊,有什么问题吗?”仿佛颓废是一种时髦,小姨理直气壮得很。
我的小姨生于1970年,87级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本省一个偏僻的小城。当年,外公努力想办法要把小姨调回我们家所在的省城,小姨却完全不配合,努什么力呀?在哪不都一样活着?她自作主张卷起包袱去小城那家单位报到。至此,小姨离开了外公外婆的怀抱,邪邪乎乎独自生长。外公说,就像一棵发育不良的歪脖子树。
我喜欢跟小姨待在一起,她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松松垮垮,相处起来一点不像长辈。过年过节她会从300多公里外的小城回来,放寒暑假,外公外婆也会带着我去她的那个小城,跟她住上一段日子。不过,这“一段日子”,大抵也不会超过两周的,小姨嫌家里人多,烦。确切地说,小姨其实怕被人管,任何一个他人都会打搅小姨多年的独身生活,这个“他人”,自然也包括父母。他们都说,小姨一贯追求自由。在我的理解里,自由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管,狂吃鸡翅和薯条,把可乐当水喝,把电脑当书本看。可是小姨想要的自由实在让人看不懂,就像她喜欢的那张画——在小姨的卧室里,摆着一张躺椅,椅子正前方墙上,除了挂着一台电视机外,还挂着一张画。小姨说,这是一张世界名画的复制品,名字叫《自由引导人民》。这张画常年挂着,从没更换过。有过一段时间,我不太敢去看那张画,那个举着旗子在战场上指挥人们的女人,上身裙子滑到了腰上,露出两只胖胖的乳房让我很难为情,会不断联想到自己正在像小馒头一样涨起来的胸部。后来有一天,我在美术课本上看到这张世界名画,感到十分亲切,就好像看到了小姨的旧照片。
小姨常常窝在躺椅上抽烟,看看画,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头顶的天花板上便洇出了一大圈黄,遇到梅雨天,潮湿格外严重的时候,人坐在躺椅上,会被一滴滴油一样的黄色水珠打中。小姨懒得去擦的,反觉得有趣,抬头去数那些凝在墙上的“黄珠子”。
这张画是师哥送的。师哥是大学时的学生会会长,我在小姨的相册上看到过他,中等个子,瘦瘦的,拧着眉头,表情的确很“学生会”,长得有点老。我怀疑地问小姨,师哥很多女同学追?小姨眨眨眼,想了想,说:“是的。他当年可是个人物呢,有理想,有信仰,有激情……”“噢,师哥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呀?”小姨一问三不知:“可能,失踪了……”“啊?那么大一个人,怎么会失踪了呢?”小姨迟疑地摇了摇头。据小姨说,师哥大学都没念完,后来,就杳无音信了。
我猜小姨喜欢师哥,不过,是暗恋的那种,小姨会不会因为暗恋师哥,变成了一个“剩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小姨太伟大了。我算了一下,应该有二十年以上了,oh,my god!我觉得小姨简直就是——虐!
小姨在家里实在待不住了,会带我到游乐场玩一把,玩刺激的青蛙跳、摩天轮,在人群里她的叫声是最尖的。小姨还喜欢刮刮福利彩票,二十块买上十张,认真地问我,小嫣,这张会不会中?我说,中!当然,一次也没中过。“鬼信!”小姨笑着走开了,并不觉得那是输钱。
在玩这方面,我跟小姨是没有代沟的,我玩什么她也玩什么,只是在玩够了回家的路上,小姨一下子就变了,她忧郁地揪揪我的小胖脸说:“人啊,活着都是没意思的,总体来说都是不高兴的,只有游戏里那几分钟时间是高兴的,小家伙,你说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心里盘算着要怎样才能多吃到一只香芋雪糕。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小姨说,要坐下来,吁根烟再走。刚好附近有个书报亭,书报亭前摆着个雪糕柜,我终于如愿。对着大马路,我和小姨两个人坐在大榕树下,一个手里举着支雪糕,一个手里举着支香烟,各自幸福着。小姨连续抽了两根烟,烟头往地上一扔,脚尖一搓,抡抡手臂,好像跟空气里的谁打招呼:“回家喽!”
回到家,我向外公外婆汇报今天出游的高兴事,外公看看小姨,没了抱怨的念头,俯下身来,摇摇我的手说:“你看,小姨对小嫣最好了,小嫣长大了要像孝敬妈妈一样孝敬小姨哦!”我重重地点头说:“嗯,我长大赚了钱给小姨买烟抽!”小姨笑了。她的眼睛里红红的。
离开小姨家,走到楼下不远,我转头回去看,只见小姨站在3楼的阳台上,挨着两盆芦荟边,右手举在耳朵旁,两根手指做成一个“V”的形状,好像在等人拍照的样子,见外公外婆也转过头来,她的手才垂到栏杆底下。我知道,小姨的“V”字里,夹着根香烟。外婆说:“小妹这样下去,怎么办?总是高兴不起来。”外公看了一眼远处的小姨,狠狠心,扔下一句话:“没头脑,自作孽!”
小姨站在阳台上,抽着烟,目送我们离开的次数有很多,等到有一次,我忽然体会到离别的伤感滋味时,已经十三岁,青春期正躲躲闪闪地在我的身体里抢地盘,而小姨已经不动声色霸占到一个“资深剩女”的地位。
我妈多次郑重其事地对外婆说:“妈,您一定要说说小妹的,女人一定要有个家。不生小孩可以,但婚是要结的!”外婆很是赞同我妈的观点,连连点头,在此基础上她又强调了结婚的重要性。二人在这方面高度一致。结果,外婆长吁一口气对我妈说:“要不,你去跟小妹说说,你们是两姐妹,你的话她能听得进去。”我妈盯着外婆看了几秒,溜走了。
只要有小姨在场,但凡涉及结婚、生子、老有所依之类的话题,无论谁起的头,都不会有第二人敢接下去讨论的,仿佛当中埋了个地雷。倒是小姨,偶尔会大大方方地接过话题,向大家公布:“我嘛,以后肯定是自己去老人院的,要是能有幸猝死,省了病痛的折磨,那就是积上大德了,要得了大病,半死不活的,我就自行了断,活那么长干吗?!”她讲得轻轻松松,干脆利落,现场人人面面相觑,无以回应。外婆只好挥动手中的筷子,假假地在她脑袋上敲了一记:“说什么呢,死不死的,在吃团圆饭啊!呸!呸!呸!”小姨朝我扮个鬼脸,给自己塞了一口饭。
有一天,小姨要我咧开嘴巴,研究我的矫牙钢箍,看了看,摸了摸,羡慕地说:“小嫣真幸福,将来会有一排整齐漂亮的白牙。”
在我们的家族里,小姨微微突出的嘴巴是个异类,并非出自遗传,而是后天的龅牙造成的。我妈说,杨天高就是被小姨的龅牙吓跑的。我从没见过杨天高,可杨天高却像我们家族里的隐形人,一有机会就出现。“现在想想杨天高这个人最合适小妹了,可惜了……”“这个人长得好像一个人耶,呃,像不像那个杨天高?”……杨天高大概曾经是小姨唯一靠谱的男朋友,虽然他仅仅是个小公务员,但是,我们家里人都认为他曾经是小姨命运的特派员,是专门来拯救小姨的。可小姨却放弃了这根救命稻草。“太麻烦了,谈恋爱,结婚,生子,造一个生命到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再受一次罪,有什么意思?”
外婆拼命做小姨工作:“不是那样的,结了婚,结了婚就会好了,日子总是一天一天好起来的。”
“怎么可能会好起来?学习那么辛苦,工作压力那么大,贫富差距那么大,整个环境那么恶劣!”
“现在比过去好多了,过去我和你爸爸,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46块钱,养四口人,一根香肠要分成四段,一口就吃光了,你们小时候真的生不逢时,现在可不一样了,不愁吃不愁穿,什么东西都不缺……”
小姨懒得听外婆忆苦,她想说的根本不是这些。
外婆多次严肃地警告外公:“小妹的人生观很成问题,很有必要矫正!”
可是,人生观跟人的牙齿何其相似!乳牙更换掉,新牙按秩序刚排列好,牙根还没站稳的时候,对付那几只歪邪、出格的牙齿,我的矫牙钢箍就像紧箍咒般起作用,但要对付一副已经咀嚼了几十年、牙根已经深扎牙床大地的牙齿,任何方式的矫正都是徒劳,除非连根拔起。同样,要想把小姨稳如磐石的人生观连根拔起,除非小姨的脑子被洗得一干二净!可这世界上谁发明过洗脑器?
有一段时间,我妈总把我跟小姨扯在一起。我不止一次偷听到我妈在厨房里悄悄问外婆:“妈,您说小嫣将来会不会像小妹那样?”外婆生气地打了我妈一下。“少发神经啦,小嫣又不是小妹生的,怎么可能像?你自己的女儿你都不了解吗?”“啊唷妈,我都愁死了,小嫣叛逆得太厉害了,谁都管不了她,啊唷,我现在只要一想到小嫣不听话,整晚都不能睡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跟我妈顶得厉害,她也会口不择言,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出来:“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牛鬼蛇神,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简直跟你小姨一模一样!”我立即就会顶回去:“小姨怎么啦?我就是要学小姨,我偏要牛鬼蛇神!”我妈气得再说不出话来。
在我妈看来,小姨的叛逆期永没过完,她做法奇怪,想法更古怪,是一个异类分子。除了婚姻问题,她最无法理解的就是小姨的运动方式——独自爬无名山。小姨喜欢找那些无人问津的无名山爬,在爬山的时候,又爱觅偏僻的山路,甚至野路来走。我跟她去爬过一次无名山。那山虽说就在郊区,却极少人去,就像被抛荒了多年的一堆垃圾,连苍蝇都没兴趣钻了,可小姨偏偏喜欢钻那山。沿着一条几乎看不出是路的路,小姨手脚并用,撩开杂草,不时踩平一根顽固的拦路枝条,她熟络地朝前方攀登,胸有成竹,仿佛只有她才知道,无限风光就在不远的顶峰。我跟在小姨后边,沿着小姨踩平的路,一声不吭,只盼望早点下山。好在,这是个小山包,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我们就登到顶了。这个所谓的山顶大概也是小姨自己命名的,仅仅是一个稍微宽阔一点的平台,只是杂草少些而已。我呼吸一口空气,环顾左右,看不到任何风光。也不知道小姨为什么要跑到这种破地方!我在心里后悔死了,还不如待在家里看几集《海贼王》!唉,小姨真是无聊。
小姨对爬无名山的兴趣一直不减,任谁劝都不停止。好几次,小姨的手机一整天都处于“无法连接”的状态,我们吓死了,想着,再接不通,明天一早就要跑到小城的无名山去寻人了。好在,通常最终都能听到小姨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过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打火机响,小姨嘴里便一阵含糊——唔,到家了……
我妈劝过小姨:“你这样很不安全,荒山野岭的,要是遇到坏蛋,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谁来救你?”小姨耸耸肩,无所谓地说:“我这个人,要啥没啥,劫财还是劫色?”我妈哭笑不得,反问她:“你说呢,你想劫财还是劫色?”小姨笑笑,干脆地说:“财没有,色倒还剩几分,拿去吧!反正荒着也是荒着。”我妈也笑了,推了小姨一把。第二天清早,我妈拉着小姨出门,也不说去哪里,走了十五分钟到时代广场。这是我们城北比较大的一个广场,紧挨着运河边。远远的,就能听到大喇叭吵吵闹闹的,舞曲带来了好多人。我妈直接扯着小姨到东边。那里已经有十来个人在跳舞了,舞步娴熟、轻快。我妈撇撇嘴说,西区那边是老年队,这里是我们的队伍,来,你也来跳跳,很简单的,你不是要运动吗,这种运动最好!说完,我妈就加入到了那十来个人当中。小姨朝西区看过去,那里的人数比东区多出很多,她们不能说是在跳舞了,只是扭动身肢,活络筋骨罢了。
小姨并没有参与到队伍中去,任凭我妈在人群里起劲地朝她挥手。她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开始沿着广场的四边,慢慢地走一圈。她走远了,喧闹的舞曲逐渐被她关小了音量,这时,她才把目光伸向了广场中央的那尊塑像。塑像不是巨型的,无须仰头,就能看到人工铸造的五官和笑容。小姨缓缓走近塑像。塑像就跟小姨站在一起了。小姨才看清楚,在他身上几个呈现弧度的地方,搭着几件运动者脱下来的外衣,在他站直的长腿边,倚傍着几把扎着红缨子的长剑,他垂下来微微握拢的拳头上,塞着塑料袋包裹的几根油条……小姨朝他咧开嘴笑了。一会儿,她绕过了他。她也绕过了那群拍手扭臀,锻炼热情饱满的人们。她从广场的一个缺口处溜了出去……
“老妹这种人,典型一个反高潮分子,这方面到底像谁?”我妈无奈地问。外婆极力要撇清遗传的关系,翻出一个旧相册,指给我们看。一张,小姨穿着双排扣列宁装,马尾巴梳得高高的,手握一本书,表情很是“英雄”。外婆说,这是小妹读小学,参加全省演讲比赛呢。一张,是少女时代的小姨,穿着花连衣裙,站在湖畔垂柳下,跟女同学手挽着手,头稍微侧着,笑容很甜;还有一张,是几排人的合影。外婆戴着老花眼镜,把照片拿远了仔细找,指着第二排中间的那个人说,你看,这是小妹在入团宣誓呢。果然是小姨,右手握拳,举到脑袋边,嘴巴张开,显得挺激动的。“你们看,小妹以前还是蛮合群的嘛!”外婆惋惜地说。
除夕夜,一家人坐在沙发上边看春晚,边聊天嗑瓜子,外婆又拿出那本相册,指着照片对小姨说:“小妹,你看你以前,多好。”小姨没吱声,一张张看过去。外婆又叹口气说:“小妹,我还是喜欢那时候的你!”小姨就丢下相册跑到阳台抽烟去了。
小姨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小嫣,你会跳兔子舞吗?”“是像兔子那样蹦蹦跳跳吗?”小姨在客厅里,一边哼着曲子,一边把双手伸直向前,脚上随着节奏跳起来,步伐很简单,就是双脚不断地前前,后后,前前……小姨跳得气喘吁吁。她告诉我:“这就是兔子舞,双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膀上,几百人在操场围成一个大圆圈,蹦蹦跳跳,这是我们大学时代的圆舞曲,毕业那一年,一个大圆圈跳着跳着就散了,各自抱头痛哭!”“为什么呀?男生也哭?那么多人,一起哭?”我简直不能想象。小姨很自豪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是啊,我们很团结吧!”小姨把我拉起来,说教我兔子舞。两下就学会了。我们两个从这个房间蹦到那个房间,累了,一头扎到床上!我大声地喘着气,而小姨却安静得像睡着了一样,等我凑过脸去看,发现小姨闭着的眼睛,流出了眼泪来。我觉得,小姨肯定是想念师哥了。
后来,我们硬拉小姨到时代广场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礼花在天空华丽飞舞,我们在人群中欢呼,直喊得口干舌燥。要散时,才忽然想起一直落后的小姨不见了,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挤出了人群外,孤单得像电视剧里那些失恋的女主角。等到师哥重新出现,小姨已经人届中年。干瘦,满脸黄斑,一副烟嗓使她听起来比看上去还要苍老。每天,她沿着护城河,骑电瓶车上下班,烟瘾上来,便把车停下,双脚踮地,点根烟,看河边垂钓的下岗工人。那么多天了,她从未曾见过他们收获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从没钓到过鱼,还是,她一向悲观主义者的眼睛里压根就看不到生活中的欢呼雀跃?师哥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这是一个怎么看都陌生的号码。小姨本来不想接的,不过这号码太执着了,那首《秋日的私语》就快要奏完了,钓鱼者都快要转身来抱怨那声音吓跑了鱼。
差点被拒听的这个电话让小姨感到阳光灿烂,一来因为师哥说他出国二十多年刚回,费老大劲儿才找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二来,她不断温习这个惊喜的电话后,得出一个结论——师哥没变,如同这个电话一样,执着。谁也不会知道,这种执着曾经难以想象地深深吸引了她,无形地影响了她的人生。小姨执着地燃烧过,又执着地让自己变成了冷灰。如今,二十多年后,师哥如同一只走失的信鸽,翻山渡海,从远方又飞近来了,这只信鸽的翅膀扑扇着,将那堆冷灰腾了起来,在记忆的天空中舞蹈,并试图在滞重的岁月后再扬起那种血气方刚的风姿。
那天,小姨要去三亚参加同学会,从小城赶来省城的机场坐飞机。我从没见过小姨这种样子。她穿一条真丝连衣裙,外罩一件崭新的皮衣,隔着饭桌,我都能闻到羊皮的气味。
小姨说起这次将要参加的同学聚会。组织承办者是班上一名体育特招生,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对集体活动却总是热情高涨,他毕业后分到海南,现在是一间私立学校的校长,腰包涨得很,这次聚会,吃住行玩他一人全负担。小姨还破天荒地跟我们提起了师哥。她认为,毕业那么多年,这种同学聚会头一次举办,完全是因为师哥的出现,又把一帮子当年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了一起。
“师哥还是相当有领袖魅力的!”小姨说完,想了想,开心笑了。
“那师哥是做什么的呀?”我妈认为那师哥肯定很有来头,竟能指挥一个阔校长包办下几十人的费用。
“呃,师哥在电话里没说,他说这些年一直在法国,回来不久。”
“噢,海归啊,那就是大款喽,成家没?”我妈找到了话题,顺带给我们谈起了现在的婚姻市场行情。据她看过那么多档相亲节目后得出一个结论,小姑娘特别欢迎海归。海归,并不是指出国深造回来的归客,而是指那些在海外市场打拼积累了财富的大叔。“这类人啊,既有成果,又有海外身份,小姑娘们抢得步步惊心呢!”在这方面,我妈一直是家中权威,她的话基本上没人会去挑战。看起来,小姨这一次心情的确很好,她没像过去那样泼冷水,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冷笑。算是客气了。
我妈在饭桌上高谈阔论。小姨把我扯到一边,掏出一张钱,让我到附近的东利文具店买几副扑克牌。我轻蔑地对小姨说:“小姨你太过时啦,现在没人要玩扑克了,三国杀才好玩。”小姨抬手试图拍我的脑袋,却只能拍到我的肩膀——我已经比小姨高出一头了。“小鬼,又不是跟你玩!我告诉你啊,以前我们班同学打老K最凶了,基本上每个宿舍门口都摆着一摊,不分白天黑夜打,真壮观啊!”小姨是怕同学聚会时想玩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买,所以买了五副扑克备着,可见小姨是多么盼望这一次聚会啊。
小姨拖着一只亮壳拉杆箱,穿着同样发亮的黑皮衣,出门,下楼。我从窗边看下去,尽管她很快就被楼下的树挡住了,可还能听到那笨拙的“噜噜噜”响的拉杆箱,仿佛她牵着一个队伍。我忽然冒出一个浪漫的想法,我希望小姨从此不要再回来了,就像一个奔向新生活的勇敢女人一样,跟上她那些志同道合的“队伍”,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闯荡,干一番有意义的大事,而我呢,熬到明年6月高考结束,书本一烧光,也到这个世界上去,拼命赚钱,赚够钱之后就当个背包客,去旅游去探险,从此自由自在。事实上最近我常常做这种有关自由的假想,而这类假想,无一例外地被现实逐个击破。
三天后,小姨又牵着那只“噜噜噜”响的拉杆箱回来了,她打开它,掏出一大袋东西:大红鱼干、海螺片、虾米、沙虫干……那是同学会的赠品,都纷纷地装进了外婆的储物柜。此外,她还从钱包里翻出一套票券送给我妈,说是度假游的赠券,可以招待一家三口。那是在我们城郊新建的一个生态旅游度假村。我妈看到票券上介绍的项目种类繁多,顿时来了兴趣,连问了一些情况,小姨只轻描淡写地答了一句:“是师哥投资建的。”这简直应验了我妈当时的话!她得意地说:“我就说嘛,海归的这类大款,就是有搞头!”我妈其实还想继续问那个师哥的情况,不过看小姨很不耐烦的样子,只好作罢。
小姨把从同学会上带回的东西全都掏出来了,包括睡在箱底的那五副扑克牌——它们连包装都没拆。
这次外婆硬要小姨多住一天,因为再过五天就是小姨的四十二岁生日了,外婆想提前给小姨庆祝。在我的印象中,小姨是个没有生日的人,因为她一直孤伶伶地在外地生活,我们都凑不到一起给她过生日。外婆早就想好了,趁小姨这次来,给小姨过一次生日。可小姨坚决不要过生日,她反复说自己从来不过生日的,她对这些仪式感到最肉麻了。我们则在一边七嘴八舌地劝她,像挽留一个过于客气的客人。最后,一直沉默不语的外公从沙发上站起来。我们以为他要下死命令了,谁知他长叹一声,对小姨说:“你考虑考虑吧,你妈和我都快80了……”话说一半就没了下文,自顾朝卧室扬长而去。
在家庆祝生日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晚饭多出了几样菜,打开了一瓶红酒,每人轮流举起酒杯向寿星小姨祝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小姨做起来却显得那么尴尬。切生日蛋糕的时候,她干脆久久地待在阳台上抽烟,直到我们把蜡烛点好,灯灭掉,喊她,她才走过来。
看起来,柔和的烛光终于让小姨自在了一些。她会跟着我们一起拍手唱生日歌,逐渐融入我们这个集体。她凝视着那些蜡烛,目光亮晶晶的,仿佛过生日的人不是她而是这只摆在中央的大蛋糕。唱完歌,外婆催促小姨许愿。小姨只好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我发现外婆也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巴动了动,像她在寺庙拜神的那样。
蜡烛吹灭,灯光重新亮起,我们拔蜡烛准备切蛋糕,小姨忽然好像神经发作般,用手在蛋糕上抓了一把,在我们还没能作出反应的时候,她的手往我脸上一抹,弄了我一脸的奶油。小姨这么幼稚的举动跟她四十二岁的年龄以及一贯沉闷的性格太不相称了。我们都感到很怪异,仿佛她被什么灵魂附体。
就像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画面一样,那个蛋糕被我跟小姨你抹一把我抹一把的游戏浪费掉了。小姨狂笑不已,看上去简直像个疯子。最后,她竟然把整盘蛋糕都盖到了自己的脸上。
无论如何,大家为小姨这突然而至的疯狂感到难以理解,隐隐觉得:小姨一定受什么刺激了。
当天晚上,我跟小姨睡一床。睡到半夜,我就被声音吵醒了。小姨睡的位置是空的,那声音代替了小姨在黑暗中起伏。我一动不敢动,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凭感觉找到了那声音的所在地——靠墙的那只落地大衣柜。小姨把自己关在那里面,正试图放低声音哭泣。我听了一会,鼻子就酸了。我想,失恋,大概就是这么伤心绝望的吧。可怜的小姨!
几个月后,我在郊区那个“绿岛生态旅游度假村”见到了师哥。他在满墙的大照片里,跟好多人握手合影。那些人,用我爸的话来说,都是些“大人物”。我虽然从没见过师哥,但相比小姨相册中的那个清瘦师哥而言,他变得实在太多了。他已经变得圆乎乎的,正面照,两只耳朵已经看不见了,侧面照,鼻子被深深地埋藏住了,一笑,满脸的肉都在放光芒。他总爱穿阔阔的唐装,黑的、白的、花的……在不同的相片中,人再多我也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整个度假中心,随处可见师哥跟“大人物”的合照,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那张巨幅照片:他屈着脊背,在跟一个“大大人物”握手,手腕上戴一串佛珠让我记忆深刻。这些照片一张张看过去,除了几个明星之外,那些“大人物”我都不认识,可是,我爸却对他们相当“熟悉”,他说,这里边,有新闻联播的常客,有财经杂志的封面人物,还有体育明星、网络论坛的公知分子……“额的神啊”,我爸佩服地说,“这个师哥还真能混啊,什么界都能搭上,太牛了!”
这个度假村其实就是一座山。师哥把整座山都包了起来,温泉、高尔夫、射击场、农庄……要是可以的话,一个星期都玩不完。我妈说,其实这里并不合适家庭度假。那适合干什么?我妈眨巴眨巴眼睛,暧昧地说:“适合这些人来,搞腐败!”她指了指墙上的照片,迅速跟我爸交换了一个眼神。
托小姨的福,我们一家三口在“绿岛生态旅游度假村”好好地“腐败”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凭赠券领取了度假村自己研制的农家保健品——两盒标价为2800块的绿色螺旋藻。又白玩又白拿,我妈满意得要命。离开度假村时,她望着车窗外远去的青山,怅怅地说,老妹怎么当初就不跟师哥好上呢?
小姨是绝对不可能跟师哥“好”上的,当初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比起师哥的改变,小姨现在的改变更让人可怕——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怪阿姨。原来,反高潮主义者伸出手来制造高潮另有一套,那就是——搞破坏——就像破坏她那个四十二岁的生日蛋糕一样,她把命运分配给她的那部分蛋糕,毫无耐心地一下子捣碎,如同玩各种不同游戏,她从中获取短暂的快乐。比方说有一次,小姨到邮局给外婆汇款,电脑排序票上显示,她还需要等待四十八人才能轮上。反正无所事事,她就坐在大厅里等。等着等着,她发现,很多人拿了号之后,没耐心等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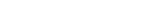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